Lucas Debargue 專訪:藝術家必須自我挖掘,儘可能地深
抱歉我語文能力貧弱,只能二手翻譯。懇請俄語人士不吝指正。
----------
記者:第二次來莫斯科,感覺怎麼樣?
法魯:跟之前一樣棒。尼金斯基大街好像比兩個月前更漂亮了。
記:你最近說到過去在巴黎,你的生活近似昏迷,而在莫斯科,打開了一個全新又神聖的世界。
魯:沒錯我在巴黎也有生活圈,但「昏迷」這字眼好像嚴重了點。不過,巴黎就像許多其他的大都會,人們看見卻不會注意彼此。而在柴賽的氣氛,就充滿了溝通與融合,那股能量從音樂廳一直滿到外面大街上。在莫斯科,我感受到一股生命的衝動不可思議的加強了。在巴黎,從來沒感受過。
記者:從來沒有?
魯:沒有。
記者:最近有媒體刊出了個世界友善城市排行榜...
魯:...莫斯科是最後一名!對,那個我讀過了。一派胡言。在莫斯科我覺得自己像個王子。這個排名是根據觀光客的意見,跟我的經驗不同,畢竟我是被邀請來的。順說,巴黎對旅客也不怎麼好。
記者:所以,所謂巴黎是世上的天堂,這對你只是個神話/迷思而已?
魯:巴黎是個非常美麗的城市!用巴爾札克的話來說,每一個街道都有一篇全新的小說。但是這城市跟巴爾札克的年代比,已經改變非常多了。街上充斥的都是工商業,很辛苦的。巴黎不像莫斯科,巴黎很小,到處都是人,到處都擁擠不堪。人根本沒辦法集中精神去思考。步調快,沒有深度。然而一個藝術家最需要的就是往內挖掘自己的深度,要儘可能地深。
記者:你最喜歡的作家之一,杜斯妥耶夫斯基曾說過,在人群中最容易感受到孤獨。
魯:是啊,愛倫坡也說過,波特萊爾也說過同樣的話。當我們回想十九世紀的人是怎樣時,就會發現如今人們都改變了。大家都把自己埋進手機裡,這裡面甚至連人性都沒有。在都市裡我並不是覺得孤獨,我是覺得空虛。人來人往和資訊洪流,把我的精力都榨乾了。
記者:埋進手機裡以後,爆炸的資訊就更多了。
魯:一點沒錯。所有的資訊都很空洞,因為他們都無關愛、無關靈魂、無關存在的意義。但我只想要談論這些。
記者:比賽期間,你的粉絲很驚訝的發現他們的偶像竟然沒有臉書帳號。現在他們知道為什麼了。
魯:我上網是為了找音樂、聽音樂、下載樂譜。儘管這樣,就可以每天淹死人了。垃圾、無腦的東西實在太多了。假如我去玩臉書,我就沒時間給音樂了。為什麼音樂會如此美,因為它可以讓你片刻間向幾千人交談。在我看來,音樂家和聽眾不該在聽完音樂會後溝通。我認為在後台聊這些是不對的。我們已經在音樂中結合,心裡已經有一幅圖像,是這個藝術家的圖像,我們還試著用意識去捕捉這種無形的藝術。這已經夠糟了,如果沈迷在其中就完蛋了。因為音樂的真理只存在於音響中。
記者:你從來不把音樂圖像化嗎?
魯:我看到一些畫面,但那不屬於思考的過程。並不會有個什麼相簿或畫廊之類的。這些畫面比我龐大,我只能沈浸在裡面,投身其中。而且是有生命的,我可以與它們互動。
記者:就像夢境?
魯:是的。
記者:柴可夫斯基大賽有個很重要的傳統,打從第一屆范克萊本那時就有的:莫斯科的觀眾,特別是女性,會瘋狂愛上那些擁有俄式熱情又才華洋溢的外國鋼琴家。你覺得這個傳統造就了你現在的名氣嗎?
魯:我想是吧,但我不確定。因為我專心比賽,那些激動的情緒並沒有影響到我。
記者:你曾說過在莫斯科的演奏並不是你最佳的表演,但你的才華卻是在此地得到認可。
魯:因為這是柴可夫斯基大賽!這也不是唯一的頂級比賽,還有蕭邦、范克萊本、伊麗莎白女王大賽。柴賽的精神是很特別的,也許就是因為這許許多多的傳統。我想我變成這獨特世界的一部分,得要找出一條路走得更深入點。
記者:你就像范克萊本,有個俄國學派的老師。Rena Shereshevskaya。
魯:是的,所以我感受到自己與這學派的連結。跟Rena上課很激烈的,倒不是說我們都在吵架,而是我們好像一起飆車,一路衝向音樂那樣。
記者:你是否同意比賽四輪中,你的第二輪表現最好?
魯:當然囉。
記者:為什麼?
魯:第一輪有一套指定的曲目,而且我是第一次登上柴院大廳。到第三輪我已經累垮,要一直打起精神。我以前跟管弦樂團演奏過,但是沒有這樣連續兩首協奏曲。而第二輪選的曲子是我真心想要彈的,我非常了解這些音樂,每個音符要怎麼彈我都非常清楚。全部都想得很透徹。
記者:他們(今晚音樂會主辦單位)特地從日本運來你比賽時選的那匹「戰馬」,同一台Yamaha鋼琴。
魯:我不知道耶,真是驚喜。對我來說這架鋼琴給我最棒的回饋,我彈起來最舒服。選鋼琴不是因為聲音美,而是因為彼此相容。
記者:跟葛濟夫一起參與Merano的音樂節,狀況如何?你們合得來嗎?
魯:太棒了。我覺得很有信心。一般說來對音樂家,要建立自信是很不簡單的事。大家都認為,技術的掌控是鋼琴家關鍵的品質。但奇怪的事就是,假如今天鋼琴家A彈錯一堆東西,可是他總是保持穩定又強健的風格,大家會說他是個技術好的鋼琴家;鋼琴家B從不彈錯音,可是他氣質虛浮不穩,大家就會說他技術不好。對我來說,脆弱和不穩定是最重要的。因為比音樂強勢是不對的,你不是大師,音樂才是大師,甚至作曲家都不算。音樂比演奏者和作曲家加起來都更巨大。我自知在音樂這個巨大的山峰面前,我既弱小又無助,可是我不會想要登到頂上插個旗子說:我征服了音樂。彈出爆炸多的強力八度,快到不能再快的速度,然後聲稱「我好愛音樂!」,那是騙人的。音樂給我喜悅,也沒有少給我痛苦,我既愛又恨。因為有時候他會把我內心吃光。葛濟夫知道也了解這些,跟他合作我不僅感到自信,也覺得十分自由。葛濟夫給了我承諾,完成了所有的我想說出來的東西。
記者:葛濟夫一年有三百場音樂會,你會走上這條路嗎?
魯:現階段不可能。假如我有能力一年開三百場,我想我會。
記者:你有專屬經紀人了嗎?
魯:我還在找。
記者:你知道如何說不嗎?
魯:不知道。
記者:真是令人印象深刻。
魯:其實我很想接受所有出現在我面前的東西。可是我得留時間給自己。這很重要。我需要時間去思考。而且我需要時間訓練我的記憶力。
記者:你對你的記憶力不滿意嗎?
魯:我很滿意。但我每天都試著背起一些新東西:詩、散文、音樂。這是個滿痛苦的愛好,但是我越來越著迷了。我就是忍不住。我的大腦需要運作。而且這有個很大的好處:當你腦中有了這一大堆東西以後,面對任何有壓力的狀況,不管是錯過班機、或是被雨淋到濕透,你都不會驚慌失措,只會覺得溫暖平靜。這個愛好讓我找到安全感,找到防火牆。
記者:你剛說你希望多談一些愛、靈魂、存在的意義,為什麼?
魯:因為我是個基督徒。精確一點說,我正在往成為基督徒的路上走。
記者:你是天主教徒嗎?
魯:我想是的。準確一點說,慢慢往這邊去。我想加入教會。
記者:你認為音樂中情慾的能量有多重要?
魯:這種能量到處都是,不能馴服,也不可能壓制。回到1968年,我們法國有個性解放運動,事實上,這只是個假象。那之後大家都認為,我們解放了!性不再是禁忌,那我們現在又過得如何?不管是性還是愛,一切都更加冷漠,而且變得更受宰制。而愛應該是帶領我們走向有性的生活。我試著在生活的微小處感知這種情慾的能量,我曾經去過希臘,聞過沙灘的味道,聽到海潮的聲音,看到鵝卵石,我覺得一切都很性感。同樣的感動也存在音樂裡。唯一出於宗教理由讓我擔心的,是這恐怕是個虛假的誘惑。只有在音樂裡面感受這種誘惑,我不會被摧毀。所以對我來說,情慾、宗教、每日生活之間並沒有界線。但我不認為這種沒有界線的態度,普遍存在於我們當代的風俗中:每件事情都相關!我努力工作,我就擁有情慾的感動,我也沒有上教堂。性愛並不是長輩禁止,然後我們就去胡鬧的那種事。我相信在清教徒的時代,人們也知道怎樣從床上得到快樂,更不需要把這種東西印在亮晶晶的雜誌上。現在呢,關於性愛或宗教的概念都扭曲了而且蒙蔽了大多數人。政治也一樣。對我來說,信仰共和或信仰君主制,似乎都是一樣的愚蠢。自由、平等、博愛,你每天睜開眼睛都看到了嗎?回到你剛剛的問題,你是不是認為我的演奏裡沒有情慾的能量呢?
記者:你的演奏更靈性些,比較不肉慾。
魯:但對我來講那是一樣的,我不會把神聖和情慾分開。
記者:所以性對你是神聖的?
魯:為了繁殖而性,是生物本能;為了享樂而性,那是異端。如果一個人因為心中燃燒的愛無法遏止,是因為他跟另一半彼此強烈的吸引,那麼性就是神聖的。在我生命中只有過一個女孩讓我幸福的經歷過這些,那一步步走向高峰的感覺,簡直難以置信,一切都因你而燃燒,你和宇宙同在。
記者:可是沒有身體的接觸,你不會有這樣的體驗。
魯:當然不會有。靈魂脫離肉體,是邪惡的。擁有軀體的靈魂,才有可能成聖。我知道東正教跟天主教對於基督的身體的重要性,看法不一致,而這是聖禮(聖餐)的基礎。總而言之,對於這類字眼我們都要小心,因為思考這些可能會讓人發瘋,尼采跟史克里亞賓幻想自己站在比上帝還高的位置,所以他們瘋了。
記者:我想你不會面對這樣(思考這種問題)的誘惑?
魯:不會。我主要的誘惑是憂鬱,我常覺得絕望,而且真的有股力量吸引我維持這種狀態。
記者:音樂沒有幫助嗎?
魯:不,不是這樣運作的。當我在音樂裡,一切都很好,但問題是,如果我覺得抑鬱,我就不想彈琴。
記者:這是你十五歲後不上鋼琴課的原因嗎?
魯:不是。我只是孤單一個人,上了新學校,交了一群新朋友,過了一段輕鬆的日子。
記者:那為什麼中斷你的音樂課?
魯:沒時間啊。我們每天玩十六個小時呢。
(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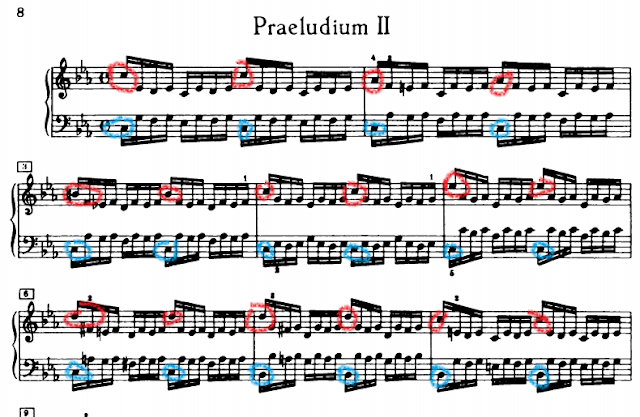
留言